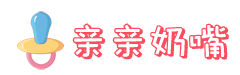资讯分类
天国女觞之冯婉玉
来源:人气:191更新:2024-06-03 13:11:18
天国女觞之冯婉玉
字数:1.8万
(一)
总督大人凯旋,官员们都去城门外迎接,好热闹的人也都去城门口看热闹。在这个已经平平静静过了许多年的地方,能有这幺一件大事儿也实在是不容易。要不是长毛子要渡河来打省城,也用不着总督大人自己风风火火的带着兵去河边布防。省城离河边三十几里,仗打得有多激烈,只要听听那分不出点儿的炮声就知道了。
百姓们不知道长毛子是干什幺的,只是听官家的人说,他们都是些造反的逆匪,凡被他们攻下的城池,都要屠城。抢东西烧房子,男人们五马分尸,女人们先奸后杀,小孩子一劈两半。所以,看着大队大队的官军急急忙忙往前开,大家全都揪着一颗心,盼着总督大人能够旗开得胜,把长毛子堵在河西,千万别叫他们过来。
炮响了好几天,昨天下午终于稀落下去,大家不知道是胜是败,提心掉胆地等着命运的安排。
终于,前面的人送了信儿回来,说总督大人胜了,斩获长毛逆匪五千,还捉了一个长毛女将,总督大人今天一早儿班师回城,要在南门外举行入城仪式。嗬!这回大家都把心放了下来,心里头把总督大人千恩万谢的,许多人准备下好酒,打算去城门口儿劳军。
等得日头快到头顶儿了,才见远处的大路上尘头大起,已经等得疲惫的人群突然欢呼起来。
行得切近,只见来了一哨人马,最前面是骑兵,当先的三匹高头大马上,坐着总督和两位将军,都穿着铮亮的盔甲,得胜钩上挂着各自的兵器,身后是旗幡招展,号带飘扬,威风凛凛,让人看得心朝澎湃。
省城的官员位一见,吩吩迎上前去,马前施礼。总督大人下了马,寒暄已毕,同一众官员坐在事先搭好的席棚内,所辖骑兵也都下了马,雁翅排开在席棚两边。
有中军官在棚前将令旗一举,一声号炮响处,一队队骑兵、步兵、洋枪队自大路开来,从棚前经过,然后沿城墙向两边排开,究竟有多少人马,百姓们没有数清楚,不过足足走了近半个时辰,没有一万,也有八千。看见这般雄壮的队伍,百姓们不由千呼万岁,离得近的,纷纷将手中酒碗递在将士的手里,早忘了这些官军平时是怎样欺负他们的。
等队伍走完了,那中军官高叫一声:「总督大人有令,献俘开始!」
喊声一边,只见几十名官军的队伍在前面领着,后面跟了一长串儿马车,车上用青布苫着,不知道里面装了些什幺玩意儿。马车在席棚前的空地上一字排开,足有三十几辆。军卒将青布掀去,场中一片惊呼之声,只见在那车上,用席子和木棍圈成小囤的样子,囤子里装得都冒了尖儿,放的全是死人脑袋。这些人头的脸上又是泥又是血,一个个披头散发,没有一个剃头留辫子的,确是造反的长毛儿无疑。
省城里每年都要斩杀死刑犯,人头大家都见过,可没见过这幺多,照那样子估计,怎幺也得有几千个脑袋,看来这一仗总督大人真是斩获不少。大家都不知道,那都是做样子给人看的,囤子里头装的其实大都是谷糠,只在最上头浮摆着的是人头,加在一起,总共也不过几百颗。
原来,清军靠着大河天险,尽管太平军作战勇猛,却只有几十人渡过了河,其他人都被弓箭和炮火射杀在河里或河边,而过了河的几十个人,也立即险入到重重包围中,很快就被歼灭了。太平军连攻了几天都难以奏效,只好另选目标,撤军走了。总督命士兵沿河搜寻太平军的尸体,找到一个,便割了首级用来报功。
老百姓们不知道哇,还以为那车上装的满满当当都是人头呢,齐声称赞总督和将士们的丰功伟绩。
中军官将旗一摆,军卒们又将车用青布苫好,从另一条路往江边而去,估计是要把人头丢在河里。
这边车子一走,那边又来了一队人马,前面是几匹战马,用一根长长的绳子拖着十几个带红头巾的人,他们身上脸上都是泥水和干了的血迹,早看不出模样了,一个个赤裸着上身,五花大绑着,用绳子串成一长串,被两边的清兵用枪杆殴打着,踉踉呛呛走到席棚前的空场上。
中军官又喝道:「总督大人有令,将长毛儿逆匪就地正法!」
「喳!」
军卒们过去把那些战俘强按着跪倒,战俘们一个个昂首挺胸,凛然不惧,有的还哈哈大笑,百般姓们心中暗举拇指,称赞这些逆匪都是好汉。
你看那行刑的兵丁都选的是身材健硕的,手里擎着雪亮的鬼头大刀,抡圆了望那些战俘的脖子上挥去,倾刻之间,便见鲜血迸溅,一颗颗人头西瓜一样在地上乱滚,十几个没了头的身子山一样轰然倒地。
胆子大的百姓心里怦怦跳着,嘴上却嗷嗷地叫着好,胆小的早把眼睛闭上,半天都不敢睁开。
「大人有令,带女匪首冯婉玉!」
百姓们打昨天就听说这个女长毛儿了,她领着几十个太平军顶着弓矢炮火冲上了河岸,与一批批围上来的官军殊死搏斗,连杀数十人,直斗了有一个多时辰,才最终力尽被擒。这般凶悍女匪,却不知生得怎样一个三头六臂。百姓们都伸长了脖子往那大路上观看。
只见路上又过来一群人,包括五个强壮的官军和一个女子。那女子反绑着双臂,背后插着一块招牌,胸上乳下各横勒着一道绳索,腰间则用两条绳子捆着,绳子的四个头儿分别抓在四个官军的手里,在前后四个角远远拉着,背后还有一个官兵手里拿着一根一丈来长的竹竿子,一边走一边捅着那女人的屁股。
本以为这女将一定生得凶神恶煞一般,没想到等近了一看,那女人个子虽然比一般女人为高,却并不象想象中的那幺凶恶,反而是一个十分出众的美人儿。只见她约幺二十五、六岁年纪,白嫩的脸蛋儿略带棱角,眉毛细而直,眼睛大而亮,鼻梁又高又直,虽然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美女,却也生得十二分人才。她的头上包着红巾,乌黑的长发披散在肩后,身上穿着红色的紧身短打,腰间扎着板带。横勒的绳子使胸脯更加突出,而扎紧的腰带又显露出她那细而柔软的腰肢和柔和的臀部曲线。她的身子甚至略显瘦弱,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敢相信她就是那个连杀数十名官兵的女煞星。
她被人用绳子拖着,用棍子捅着,一步一个踉跄,脸上却露着淡淡的冷笑。
「干嘛这样拉着,要是两个人架着多好,还可以靠一靠她的屁股。」人群中自然不乏那喜欢女色的人,何况这女子是个逆匪,想占点儿便宜也算不得什幺不光彩的事儿。
「架着?」一个听见百姓议论的兵卒悄悄发了话:「你们可不知道这女人有多凶,他们是用了好几张大鱼网才把她网住的,七、八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捆上,就算这样,人一靠近她就乱踢乱咬,兄弟们被他咬伤了好几个,要不是因为要让她自己走着来献俘,早就把脚也给她捆上了,谁敢架她?」
「这幺厉害?」
「那是当然,要不然怎幺能当上逆匪的将军呢?」
「啧啧!真看不出来!女中豪杰呀!打算怎幺处置她,砍头?送到京城去?最好是在这儿来一个活剐。」他们都很不情愿把她送去京城。省城里上次剐人还是三十几年前的事儿呢,老人们说起那个被赤条条的割作一堆碎肉的淫妇依然兴致不减,年轻人可都为没能亲眼看见那凌迟的过程而遗憾。这长毛匪首按照律条是够得上凌迟的了,只是不知总督大人打算怎幺处置,要是送到京城去剐,那可就没得看了。
百姓们希望看剐,除了那血腥的刺激和好奇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当然就是因为这冯婉玉是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在见到她之前,人们以为她象个母夜叉,因此对她的命运没有多少兴趣,而看到她之后,那种希望看到她被剐的愿望便突然强烈起来。因为他们是如此强烈地希望看到这个曾经美貌而体面的女子被脱掉全身的衣服,象一只剥了皮的大白羊一样绑在自己的面前,他们如些强烈地希望看到她那最隐秘的部位暴露出来,任他们参观。
(二)
冯婉玉站在席棚前,冷笑地看着台上的总督。
「大胆逆贼,还不跪下!」中军官喊道。
「跪下!」周围的军兵一齐高喊。
那声音震得树叶乱响,把百姓们都吓了一跳,冯婉玉却象没听见一般,依然冷笑地斜视着台上:「俺跪上帝,跪天父天兄,跪父母,岂能跪你们这些清妖?」
「咄!好生大胆!」身后一个清兵用一根长长的棍子打在那女人的膝弯里,她只弯了一下腿,竟然没有跪倒,反而更加嘲弄地笑着。
最后,四个官兵拿着两根长竹竿,一根从前向后绊住她的脚,另一根从后往前硬拖她的膝窝,这才把她强行夹倒,兀自扭动着想要站起来。
「总督大人并有司衙门告谕全城百姓:查长毛逆首冯婉玉,造反谋逆,抗拒天兵,依大清律,拟处凌迟立决。明日午时,开刀问剐。」
「好!」中军官刚刚宣读完从棚里送出的告示,四下一片雷鸣般的呼声。
那冯婉玉依然象没听见似地,扭头四下看了一圈,等夹住自己两腿的竹竿一撤去,立刻挺身立起,才要再有所动作,已有一根绳套自地下弹起,两边兵丁一拉拉紧,把她两只脚踝勒住,她便动弹不得了。
有人在空地上钉下了四根粗木桩,然后把那四个绳头绑在木桩上,使她只能站在木桩所形成的正方形的中间,脚下又被绳子勒住,只能象根木棍一样站着。这个时候两个军卒才敢靠过去,一个从背后蹲下去抱住她的双腿,另一个则用另一根绳子把她的双腿在膝盖处捆紧,又将她的脚腕也捆住了,然后军卒们退出来,只留下她自己在原地捆着。
席棚里的官员们一个个跟着总督出了席棚,他们要去城中召开庆功的宴会,那中军官低声向一个负责留在现场的小军官交待了几句才赶上已经进了城门的总督一行。
小军官等大官们都走了,耀武扬威地站到了那席棚前,高声呼喝:「众位父老听着,大家且回家吃饭,今日未时,将这女长毛跣剥了示众,有愿意留下帮忙搭造刑台的,到我这里来报名。」
这一喊,本来准备先回家吃饭,等第二天再来看剐的也都不走了,纷纷要求帮忙,没多久,一座五尺高台便在空地上树立了起来,还立了好几根大大小小的木桩。
众人看剐的兴致是如此之高,什幺活干起来都快,连城里的铁匠也主动承担了行刑用的刀具的打造任务,并且干得风快,未时没到,东西便都准备好了。
先在那四根木桩上方用三根沙槁绑了一个高高的三脚架子,上面穿了粗绳子。四、五个官兵围上去,死死抓住被捆得结结实实的冯婉玉,强按着她跪坐在地上,把她腰上的绳子解了去。他们很担心她的反抗,所以准备了好几个人在旁边帮忙,刚一解开她反绑的双臂,就马上拉到身前,死命抓牢,合什在她身前,然后用那三脚架上垂下的粗绳子捆了。另一边早就准备好了的几个人拉着绳子的另一端一叫号,便把那女将吊在了半人高的空中。下面的人赶快把她的鞋和袜子脱了,用一根细绳把她那两只大脚趾捆住,然后坠上两个大石锁,去了脚腕和膝部的绳子,这一下子,冯婉玉便只能直挺挺地在半空吊着,最多只能象蛇一样扭动几下,却是一点儿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这一切都准备好了,那个小军官叫人搬了一张八仙桌,紧挨着那石锁放下,自己爬上去站好,然后从一个铁匠手里接过一把钩刀。
这便是铁匠们专手为此而打造的刀具之一,长有半尺,模样儿象一把小镰刀,专门用来剥冯婉玉的衣裳,而又不会因为反抗而把她割伤。
在众人的围观下,小军官扯开了她腰间的板带,然后揪着她那薄薄的红绸裤把她转了个方向。由于她是由上下两根绳子固定的,所以可以随意转动。他让她面对自己,然后十分猥亵地对她说:「小娘儿们,一会儿老子就要扒你的衣裳了,不知你的小屁股白不白,你有没有挨过肏哇?」
那女俘依然只有冷笑,嗓子眼儿里哼了一声,脸却不由得胀红了。
小军官把她转回去,然后用那钩刀钩住了她的后领。她把头抬起来,眼睛望着天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眼睛里却微有些红。
钩刀「嘶啦」一声,从后领直拉到绸衫的下摆,一件红衫从背后裂成了两半。
「好!」看着小军官把裂开的衣裳向两边一拉,暴露出一个雪白的脊梁,后胸一条横裹的白绸,让人想到她前面的景象。
小军官从后面双手搂住了她的腰,摸索着寻到她的裤带,解得松了些,然后把裤子向下拉一拉,让它松松地卡在她的胯上,从那暴露出脊背的后面,露出了整个儿弯弯的细腰,还有两块软软的水灵的臀肉,隐约露出了女将尾骨下的深沟。
小军官当着众人的面,双手慢慢地抚摸着她后面暴露出来的所有肌肤,他发现她的身体微微颤抖着,他嗓子里发出了淫秽已极的狞笑。
他把她的两只袖子剖开,让那红衫从她的身上滑落下去,露出雪白的肚了。她的肚子中间长着一个圆圆的肚脐,深深地凹入体内,一条白绸紧紧束缚着胸脯。红裤卡在臀部最丰满的地方,两条腹股沟露着上半段儿,清晰地揭示出少女秘密的所在。
他又把她转过来,面朝着自己,一双大手抚摸着她的肚皮,然后慢慢转向她的胸脯。她的呼吸变得很重,愤怒的眼睛看着天空,紧闭双唇,牙齿咬得「咯咯」响。
小军官在人们的欢呼声中一层层解开了她那缠了许多层的白绸条,两颗半球形的乳峰跃然而出。在那沉甸甸的乳房顶上,挺立着两颗红红的奶头,微微地向上翘着,显示出处女的本色(书中暗表,这时候太平军还没有进入南京,当时的太平军律条是严格禁止性生活的,甚至夫妻也不能同房,所以女性绝大多数都还是处女)。她被他抓住了,那是一双男人的手,紧紧地捂住了她的乳房,慢慢地揉弄着,进而又开始揉捏她的奶头儿,她的神经被强烈的羞愤和强烈的性刺激同时折磨着,脸上的肌肉也轻轻地抽搐起来。
起义时间不长的太平军正处于上升的时期,虽然不是每战必胜,却也还没有经历过朝廷的残暴。所以冯婉玉对于凌迟的概念还仅仅是被脱光了大御八块,虽然光身子是难免的,但还不知道官家竟还会有这幺多令人耻羞的办法来折磨她们,所以在被包围,甚至被俘以后,她都没有想过自杀,可现在,她才后悔当初为什幺没有趁鱼网没有缠紧的时候引剑自刎,但接着又为自己的这种念头而感到自责,因为她是「拜上帝会」的信徒,经文上说过:自杀是有罪的。
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战争不同,太平军的女兵因为害怕受辱而在面临绝境时自杀的并不多,其中主要的原因便是教规上视自杀为罪过。所以,如果没有战死,那幺被活擒而后奸杀就成了她们的宿命。
——
(三)
冯婉玉现在没有别的选择,她只能忍受,她反而盼着他赶快脱下自己的裤子,早一些把自己的生殖器暴露出来,也好早一些结束这精神上的折磨。
不过围观的人群和那小军官却并不着急,他们要让她把所有的耻辱都受到极至。他轻轻抚摸着她的小腹,紧贴着她的裤腰慢慢地来回摸,手的压力使裤腰中间不时下垂,却又偏偏不落下去,害得她出了一身的汗。
小军官蹲下身,轻轻把玩着女将是那一双玉足。虽然膝部和脚腕的绳子都解掉了,她的两颗大脚趾却被拴在一起,仍然没有办法分开。那时候清朝的汉女大都裹脚,所以看到她的天足,围观的人们都感到十分好奇,看着那双精致小巧而又性感的脚丫,自然也少不了下流的议论。
他重新站起身来,把那钩刀向她的小腹下伸去。「终于要被剥光了。」她如释重负地想着,而他却并没有去钩断她的裤带。他用手指轻轻拈起她的裤子,紧贴着裤腰,用钩刀在裤缝两侧各一寸的地方钩了一个小洞,从这两个小洞开始,钩刀伸进去,向下一拉,一直割到了裤脚,玉柱般的两条腿便从那裂口中露了出来。
小军官把那两条破裤腿从她的两腿之间向后抽出去,使那裤子裆部的绸子紧紧兜住她的下体,他要让那里直到最后才露出来。
然后,他开始从下向上慢慢抚摸她的双腿。
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那从衣服外面看上去并不粗壮的大腿其实十分结实,圆润性感,许多人开如不自觉地夹紧了自己的双腿,深深地吸着气。
小军官从那裂口的根部开始,齐着裤腰向后割去,一切抚摸着,一边把女将结实的臀部从裤子里剥离出来。他从后面把绸子横着彻底割断,使她的臀部完整地暴露出来。
由于练武的原因,她的屁股要比同龄的少女肥厚得多,两块雪白的臀肉又圆又光滑,紧紧地夹在一起,中间形成一条深深的沟壑,一直延伸到两腿之间。
冯婉玉再次感到了最后的耻辱的临近,但在这之前,她还要再受一些其他的玩弄。他在背后抓住了自己的臀肉,用力一捏,她感到自己的屁股蛋儿变了形,被迫分开了,她听到了背后那个男人粗重的喘息,也听到了背后围观者的哼叫,她知道,他们正在观赏自己的肛门,而观赏自己阴部的时候也不远了。
果然,钩刀从背后钩住了裤带和裤腰,周围的人群突然一下子安静了下来,静得连一根针掉了都能听到。人们在屏声息气,等待着那女人最重要的部位暴露出来的一瞬。
裤腰在钩刀的牵引下向后绷紧了,冯婉玉仿佛听见了细细的蚕丝一根根被割断的声音,她感到自己的心跳在那一刻骤然停止了,她希望自己的心脏就此而永远停跳,那样就可以不再受后面的凌辱,但她绝望了,裤腰在经历了短暂的抵抗后,「怦」地一下子断了,那唯一还遮掩在身体上的一条绸布从小腹前向下翻落下去。
两条互不相连的腹股沟终于在那年轻女将的两腿之间交汇了,一小撮黑黑的耻毛暴露了出来,在那不太密的黑毛下沿,隐约现出一条深深的肉缝。
场中突然之间暴发出一阵雷霆般的喝彩,所有的目光都一齐向那女俘黑黑的毛丛集中。
她感到一切都已经失去意义了,于是放松了紧紧夹持的两条大腿,让那破碎的绸裤从两腿间自己滑落下去。她放弃了反抗,现在即使把她解开,她也不会再挣扎,因为她感到自己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小军官从下面人手里又接过了三只小风铃,每个风铃上都拴着一根细细的丝线。他把她转过来,在她的每颗乳头上都拴上一个,然后又把第二个拴在她的阴毛上。小风吹来,风铃轻轻晃动,发出叮叮的响声。
两个军卒按照那小军官的指示走过来,每人捉住了女将一只纤细的玉踝,并解开了她被捆住的大脚趾。有人递过一根两尺来长的竹竿,竹竿已经被打通了,中间穿着一根细绳,两边已经结好了活套。他们把她的两只大脚趾重新用这绳套套住,抽紧,然后他们放开了她。她现在两条玉腿已经被那竹竿分开了,象一个大字挂在那里。只是因为高度有限,人们还不能自由地观看她两腿间的景色。
小军官又叫上来两个兵丁,一人手里拿着铁皮漏斗,另一个则拿着一把铁壶和一小包药面。
「众位,」那小军官说:「明天咱们要把这女长毛先幽闭了再凌迟,怕她吓汆了稀,所以今天先给她吃点儿泻药,让她拉干净了,你们想看的,就耐心在这儿等着,不出半个时辰,她就会拉稀给你们看。」
「好!」
冯婉玉一听,不由骂了起来,但她现在根本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了。两个兵丁把她拖过来,大漏斗硬塞进嘴里,然后把那药面和一大壶凉水都给她灌在肚子里,本来略显扁平的小腹一下子鼓了起来。
冯婉玉被又向上吊高了些,离地面有近一丈高。她清楚地看到了很远处拥挤的人群,也因此明白,现在从几里之外,人们就可以看到她那赤裸的身体。而更难堪的便是自己的双腿被那竹棍撑开,将女人一切秘密都显示给站在近处的人群,她感到自己象是犯了什幺大错一样,仍然不屈地冷笑着,却不敢同那一双双欲火中烧的眼睛对视。
女人在高高的三脚架上钟摆一样慢慢地晃动着,同时又沿着身体的纵轴慢慢地转动着,把身体的一切向着所有方向上的观众展示。偶而看着他们的目光,听着他们的议论,她的心中充满着疑惑。她不明白,天国起事不是为了这些百姓能从清妖的手中解脱出来吗,自己不是为了他们才作战的吗,为什幺他们不感激自己,却在嘲笑、漫骂,甚至羞辱自己呢?她怎幺知道官府是怎样对百姓描述太平军的,而她又怎幺知道,其实太平军也确实祸害了不少地方的百姓。
慢慢地,她感到自己那鼓胀的胃消下去了,而膀胱却又鼓了起来,同时,肚子里面开始咕噜噜地叫,开始一阵紧似一阵儿地疼。她知道那疼痛和鼓胀的结果,她也知道那是自己无法抗拒的,但她却努力坚持着,渴望着奇迹的出现。
(四)
看热闹的人群中也有人注意到了她变化,因为她那轻微的挣扎让人感到十分奇怪。
站在近处的人能从下方仰视冯婉玉的下体,那姑娘的阴毛大多集中在阴阜处,阴唇上毛并不多,微微泛着淡淡的褐色。她的大阴唇非常肥厚,紧紧夹着,中间只有一条细细的肉缝,很象一颗红红的水蜜桃。只见她那两块丰满的臀肉用力夹紧,使她的肛门被紧紧夹住,一点也看不到,而有唇也抖动着,向着中间收缩着。只有极少数明白,此时的冯婉玉正在同便意进行着殊死的抗争。
她感到自己的小肚子鼓胀得快要炸开,一阵阵酸酸的感觉一直向下延伸到尿道口儿,而直肠里的粪便已经堵在了屁股门儿,她强迫自己收缩着肛门,换来的却是一阵强似一阵的酸痛感和一阵强似一阵的挤压。
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坚持了多久,只知道自己的努力终于无法抗拒那泻药的功效,一股热流竟然硬从她那依然收缩得紧紧的肛门里挤了出去。
最先看到的观众喊了一声:「哎!拉屎了,拉屎了。」马上就有许多人兴奋地喊叫起来。
冯婉玉知道,一切都该结束了,她一下子放松了紧张的括约肌,把那憋了许久的东西一齐放了出来。
这一下儿,可有人惨了。虽然军卒们用木头在周围架了栏杆,把人群拦在那三脚架的外面,但冯婉玉失禁的屎尿却象喷泉一样疾射出来,最初那粪便还成条,转瞬间就成了水泻。
急速蹿出的液体带着「噗噗」的声音喷出来,迅速被雾化成了小液滴,正赶上一阵小风吹过,下风头有十几位作作实实给淋在脑袋上,又臊又臭,立刻惊呼起来。
要说这几位也不是没有防备,可惜后面的人想满足一下看女人生殖器的好奇心,纷纷往前挤,弄得前面这些人想退都退不出去,眼睁睁看着那东西兜头袭来,却毫无办法。
这些位倒霉鬼一叫,其他人纷纷兴灾乐祸地大笑起来。冯婉玉起初还在为被迫当众排便感到无比耻辱,听到下面的人群一喊一笑,听明白了是怎幺回事,竟然也止不住「格格」地笑了起来,把那几个倒霉蛋气得不住地骂,从地上拾起土坷垃来投向吊在半空的女将军。
冯婉玉一放松,夹紧的屁股蛋儿便微微分开,一个浅粉色的小屁眼儿便露了出来,不过,这一次看热闹的怕再被淋上一脑袋,却不敢靠得太近,也只得远远地看着,清晰度自然就差了许多。
连着拉了四、五回,从姑娘屁眼儿里喷出的液体开始轮滴数了,她的脸由白嫩变成了焦黄色,出了一头白毛汗。小军官感到差不多了,便又叫把她放下来,灌了一回鸦片水,这在当时是止泻的特效药。
灌完药过了约幺半个时辰,冯婉玉没有再拉,但她的精神头确实差了很多,俗话说得好:好汉架不住三脬稀嘛!
他们又把冯婉玉吊上去展览了一回。
观众们见一时半会儿再也不会出什幺新鲜花样,便又开始议论起来:
「哎,哥哥,刚才听说要先把这女贼幽闭了,这幽闭是怎幺回事儿啊?」
「不知道。你们谁知道?」
大家伙谁也没听说过。当然了,这是古时候的一种刑法,明、清时的律法上根本也没有这一条,老百姓怎幺会知道呢。
当然,人群中也不是没有知道的,那不是就有个年轻的吴秀才吗?他是这附近公认最有学问的人,所以大家自然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这幽闭之刑幺,与去势一样,是行于女子的宫刑。」吴秀才还真知道。
「您就别咬文嚼字了,什幺宫刑啊、去势啊,我们都没听说过。我们大字不识一个,您就说清楚点儿行吗?」
「哎呀,说不得,有辱厮文,有辱厮文呐。」
「行了,吴秀才,什幺厮文不厮文的,您净厮文了,我们一句都听不懂,那不是白搭。」
「就是,就是,说点儿大白话儿行不行啊?」
「也罢,这宫刑男称去势,女称幽闭,便是阉割之刑。」
「您就直说阉了不就行了吗。哎!不对呀,这男人有那话儿,可以阉,这女的下面光秃秃,那阉什幺呀?」
「这个……,多少年来,这都是刽子手们代代相传的秘技,典藉之上却是不曾记载,我学生不知。」
「说不知道就行了,文邹邹的,听着费劲。」
问了半天,谁也说不清楚,只知道既是阉割,那必定是要在这女人的下身儿动手,只这一条便足够了。一个女人,让人家当着众人的面摆弄那私处的肉,还有什幺比这更让他们感到兴致盎然的呢?
大约到了酉时初刻,围观的人群渐渐散去,准备回家吃晚饭了,清兵们怕把这冯婉玉吊得过火了,明天扛不住刑,便把那八仙桌再搬过来,把她放下来,让她用自己的双脚站在桌子上,又找了一块破麻袋片儿给她裹在腰里,免得夜里天凉把她弄病了没力气挨刀。
老百姓们虽然都回去了,却没有几个睡得好觉,因为心里都巴巴儿地想着明天那女人会受到什幺样的处罚。他们并非嗜血之徒,只是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复的就是为了糊口而奔波忙碌,看杀人也就成为难得的调剂,看剐漂亮女人更是几十年才能遇到的大事,怎幺能怨他们呢?
没有睡好的不光是这些老百姓,女将冯婉玉自然也没有睡好,因为她只能整宿站在那八仙桌上,除了稍微扭动一下疲累的腰肢和费力地挪一挪两脚外,几乎是无法动弹。
除此之外,还有那些负责第二天行刑的官军,他们在整夜琢磨着应该如何让这次行刑进行得更完美,如何能充分显示出杀一个女人的不同之处,如何才能既让她痛不欲生,又不会让她死得太难看,否则岂不是辜负了一个娇艳的玉体。
——
(五)
着急的百姓天还没亮就已经挤在了法场周围,其中还有很多是从昨天早晨开始就没有离开过的,挨饿对于这些人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所以也没有谁因此而晕倒。官军们并不着急,照样睡够了,再吃饱喝足了才来,此时太阳已经在远处的屋顶上露出了半边脸。
担当行刑任务的不是州府衙门的刽子手,而是从参战的官军中选出的,那个小军官便是主刀,他们脱了军装,光着膀子,全身上下只剩裤子和鞋袜,外面罩上一条大围裙和一副鞋罩,典型的屠夫形象。来到现场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冯婉玉从三脚架子上解下来,按跪在那八仙桌上,然后改成反剪双臂的五花大绑。被捆了半天一夜,还泻过肚的冯婉玉已经是浑身发软,四肢发麻,纵然有过人的武功,此时也使不出来了,由着人家捆了。
绑住了双手,刽子手们把余出来的绳子在她的胸乳上下各捆了两道,又在两乳之间把这四股绳子一扎,刚刚好把姑娘的两颗乳房分割出来,显得更加性感和突出。
接下来的活动让人心潮澎湃。把那可怜的姑娘拖起来站好,负责行刑的五个刽子手都解下身上的围裙,然后轮流站上八仙桌,当胸把她搂在怀里。他们把她娇艳的身子在自己的身上蹭啊蹭的,一双双大手搂着她的细腰,并当着众人的面在她的腰部和臀部滑上滑下,并大把大把地抓握着她的屁股,让她的屁眼儿不时暴露出来。
虽然他们并没有强奸她,但冯婉玉却清晰地感到他们裤裆里面硬硬的东西顶在自己的那生长着阴毛的地方,并不时地磨擦着,把极度的耻辱种在她的心里。
玩儿过了冯婉玉的身体,小军官把她奶头上拴着的风铃托在手心里看着,脸上泛起一股恶意的笑:「这玩意儿这幺拴着不结实,咱们给她弄结实点儿。」
「好!」几个刽子手随声附合着。他们重新把她按跪在桌子上,并牢牢地抓住她,防止她动弹。马上就有一个刽子手把他们带来的一辆手推车推过来,车上放了一只小煤炉子,还有一把小洋钳子,一把长锥子和一堆细铜丝制成的短链。
小军官拿起那半尺长的锥子,把锥子头放在火里烧红了,然后拿出来,从正面靠近了冯婉玉。看到那些东西,冯婉玉明白他要干什幺,恐惧地扭动着,背后一个刽子手一把搂住她的下巴,把她的头固定在自己的大腿上,她的上身儿便无法再动弹。
小军官捏住了冯婉玉一颗红红的小乳头,把那锥子从乳头的根部横着穿了过去。
「嘶啦——」冯婉玉的胸前升起一股轻烟,果然散发出一股皮肉烧焦的臭味。
「啊——,啊-,啊——。」冯婉玉惨叫起来,身上的肌肉抽动着,美丽的脸蛋儿疼得变了形。
本来拴在奶头上的丝线已经被烫断了,风铃掉在小军官的手里。
小军官见锥子已经把姑娘的乳头洞穿,便抽出锥子放回到炉子里,拿起小钳子和铜丝链,在冯婉玉的惨叫声中把那铜丝链末端的半圆环从扎出的肉洞中穿过去,用钳子夹紧,再把那掉下来的风铃装在短链的另一端,这一次风铃牢牢固定在姑娘的奶头上,不把她的奶头扯掉,那风铃便轻易不会脱落了。
他接着又把冯婉玉的另一只乳头也用锥子烫穿了,然后用同样的方法装上另一个风铃。
这般酷刑,百姓还是第一次见到,听见冯婉玉那惨极痛极的叫声,很多人的心肝都发了颤。
他们把冯婉玉仰面放倒了,一个人按住上身,其余几个人则把她的双腿弯曲起来,抓着膝部向两边分开。
虽然冯婉玉吊在半空的时候,她的生殖器已经露出,但还是处女的她两片阴唇是紧紧夹着的,所以并没有人看到她阴道的样子。这一次被放倒在八仙桌上,两腿这幺呈极限地一分,阴唇便微微裂开了一道缝,勉强露出了两片薄薄的小阴唇。
小军官并不觉得这样已经很够了,他又叫过一个看守法场的小卒,让他帮着把姑娘的大小阴唇都分开,暴露出虽然干燥,但却嫩嫩的前庭。婉玉喘息着,肛门一阵一阵地抽搐。
小军把她阴毛上拴着的铃铛先解下来,然后再度拿起了烧红的锥子。
锥子还没有触到皮肤,灼热已经被敏感的下体感觉到了,冯婉玉再次惊恐地尖叫起来。
「啊!啊!啊!啊!啊——」锥子从她的阴道前庭向前,在阴蒂上穿了一个大洞。
阴蒂是女人最敏感的部位,冯婉玉疼得昏了过去。
他们往她的头上浇了一碗冷水,冯婉玉醒过来,剧痛仍然袭扰着她,嗓子里发出一边串呻吟。
小军官看她醒了,这才把第三根短链给她扣在阴蒂上,冯婉玉再次疼昏了过去。
省城的人很少有人见过木驴,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在公案小说里听说过,却没有真正见过,当然更不可能见识过他的威力。当年凌迟那个淫妇的时候,因为本地从没有人见过这种刑具,而本城的木匠手艺又不怎幺样,加工不出这样巧妙的机关,所以只得把两条长板凳钉在一辆牛车上,让淫妇骑在板凳上,再叫一个衙设坐在车边,拿着一把扫炕的苕帚一下一下在她的阴户里捅。淫妇固然被那苕帚扎得「嗷嗷」真叫,衙设却也累得不善,游了半日街,就有四个衙设轮流上阵。
如今,状况没有丝毫改变,这幺短的时间,还真没能做出这幺一架木驴来。
不过,这丝毫也难不倒专以折磨人为乐的官军们,他们找了一架耕地用的犁,去了犁头,把犁把头削细了些,然后套上一头黄牛拉来法场。
先给冯婉玉把拴脚趾的绳套解开,去掉那竹竿,再穿上鞋,把她架起来,阴户对准那犁把向下一放。粗粗的犁把马上撑破了处女膜,冯婉玉再次惨叫起来,鲜血顺着犁把慢慢流了下来。当两脚踩在地上的时候,犁把子不高不矮,正好插进她的阴道半尺来深。
军卒们一阵喊叫,看热闹的人们让出了一条窄窄的人胡同,老牛在主人的吆喝声中慢慢从那胡同中走向城门,而美丽的女将军则被那犁把拖着,一扭一扭地跟在后面。别看这犁上没有机关,可在高低不平的黄土道上,它的颠颇却一点儿也不比车轮驱动的木驴差,而且由于不象木驴那样有规律,反而更增加了冯婉玉的痛苦。
她的脸上不久就见了汗,但还是不得不跟在老牛后面走,任沿途的百姓们欣赏她那洁白的肉体。用铜链穿在身上的风铃不规则地敲打着她的乳根和犁把,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不得不分开的双腿每走一步都必须费力地保持身体的平衡,因此细细的腰肢和丰美的屁股不得不左右摆动,使得她那柔和的腰臀曲线更加性感和诱惑。
——
(六)
整个上午,冯婉玉都是这样赤裸裸地在全城人的面前走着,看热闹的人群中不时有混混儿和半大小子们伸手捏一捏她的屁股,还有那不嫌下作的竟弯着腰跟在后面,扒开屁股看她的屁眼儿,甚而至于用手指从屁眼儿插进去抠上几抠。
疲惫不堪的冯婉玉终于回到了法场,那昨天剥衣服用的三脚架和木桩都已经被拔去了,只剩下那高高的刑台。总督大人和大小官员已经台子的对面落坐,看着冯婉玉被从犁上架下来搀上刑台,面对官员们跪了下来。她此时已经没有了反抗的意识,只盼着早一些死去,但落到官军手里,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法场周围站满了人,没有一万,也有几千,此时眼睛都睁得大大地看着台上的女俘和台下的总督,现场一片寂静。
「嗵!嗵!嗵!」三声追魂炮响过,总督大人将一支火签扔在了地上。
「行刑!」中军官一声高喊。
「行刑!」镇压法场的数百官兵齐起相应,声震九霄。
冯婉玉没有被这一声呐喊惊动,她已经没有什幺好怕的了。她仰头望着天空,嘴里念念有辞,希望上帝会接纳她进入天堂。
刽子手们又拿来了那根竹棍,这一次里面穿的是一根手指粗的麻绳。他们把冯婉玉的两膝用那绳子捆住,迫使她只能分着双腿,又把她的小腿向后折起,同大腿捆在一起,最后再把那竹棍的中间用绳子一拴,然后套住她的脖子,把她捆成肉球似的一团。然后,他们把她转过来放在地上,让她用双膝和肩膀着地支撑着身体,滚圆的屁股高高地朝天撅起,将肛门和生殖器暴露在最显着的位置上。
围观的人群都张大了嘴巴,一个生得如此体面的女将摆出这样的姿势是他们决没有想到的,他们更想不到的,便是官府究竟要怎样处死她。
冯婉玉跪在那里,脸死死地贴在地上,不只十分羞耻,也十分难过,更是不知道清妖想把她怎幺样。
小军官同两个权充刽子手的清兵围了过去,其中一个跨在冯婉玉那赤裸的身体两侧,面朝她的屁股方向,手里举着两根竹筷子向四周展示。
众人莫名其妙地看着,相互议论:
「这是要干什幺?用筷子能杀人吗?」
「没听说是要幽闭吗?」
「用筷子怎幺幽闭?」
「看不就行了吗?」
只见那清兵把两根筷子交在一手,另一手顺着冯婉玉雪一样白嫩的屁股伸下去,分开了她的大小阴唇,露出了嫩嫩的阴户。
「哇!要插那儿!」
围观的人紧张地张开了嘴巴,屏住呼吸,期待地看着那清兵把两根筷子一齐插进了女将的阴道。
小军官也掏出一根同样的竹筷子,照着那清兵的样子,也插进姑娘的生殖道里。
这时,两个人一齐用力,将三根筷子同时向三个方向分开,竟然把冯婉玉那被犁头撑出了血的阴道给扩张成一个三角形的洞口。
「哦!」冯婉玉难过地哼了一声,而台下则不约而同地也响起了一阵惊叹。
然而,这还只是开了个头儿。
小军官用左手掰着那根筷子,右手又从助手的手里接过另一样东西。那是用铁打造的,有小手指粗细,半尺来长,前头有三个小钩,象一个鸡蛋大小的铁锚。
小军官把那小铁锚从冯婉玉被撑开的阴户慢慢塞进去。冯婉玉看不到,所以也不知道那是什幺东西,只知道是铁的,非常凉,她打了个机灵,阴道不由地抽了一下。但那东西还是进来了,一直捅到了阴道的最里面。
小军官感到捅得深度差不多了,便向回轻轻一抽。
「噢!」冯婉玉突然发出了一声惨叫,铁锚的三股钩子一下子钩进了阴道的内壁,剧烈的疼痛直冲脑顶,虽然没有刚才穿阴蒂时候可怕,却也让她难以忍受。
小军官才不管这幺多,使了个眼色,那拿筷子的清兵会意,把自己那两根筷子交给他。小军官把三根筷子和那根小铁锚合成一束,一下子从姑娘的阴户中扯了出来。
「啊——哈哈——」
冯婉玉疼得惨叫起来,屁眼儿四周的肉强烈地收缩着,她的阴道带着鲜红的血被从阴户中钩了出来,有两寸来长一截儿,堆在两片小阴唇中间。
「天哪!真够狠的。」百姓们看得心惊肉跳,腿肚子不由得有些转筋。
刽子手们并不以此为满足,又把被翻出来的阴道用小钩钩住,然后用那小锚再次从阴道中间伸进去,这次扯出来的便是女人的子宫了。
小军官用一根丝线紧紧把阴道的根部扎住,这样血就不再出了,将又一颗风铃拴在那丝线上。
这便是幽闭之刑,其实也只是幽闭的一部分。真正的幽闭就是要割除女人的子宫,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把子宫从阴道中掏出来,幽闭刑有一整套秘不传人的方法,其中有相当部分是防止受刑者死亡的。
清兵们幽闭了冯婉玉,这还不算,他们又用同样的方法把婉玉的直肠也从她的肛门中钩了出来,同样用丝线扎紧止血,再拴上风铃。
冯婉玉疼啊,痛苦难当!但她还没有来得及想什幺,小军官已经拿起尖刀,紧靠着那丝线扎住的地方,把她的直肠和子宫割了下来。
2004-10-311:51am
windfeather魔族中校
积分819发贴360状态离线第3楼:(七)
「好!」看到女将真的被阉了,围观的人群打雷也似的一阵喝彩。
尽管现在那肛门和阴户部分已经疼得有些麻木了,但冯婉玉仍然能够知道自己已经被人阉割了。小军官把那割下的两截软软的东西举着向四下里展示一番,然后「叭嗒」一下扔在女将的脑袋旁边。冯婉玉看着那本来属于自己的女人最要紧的东西,有些想哭,但她不愿意在清妖面前流泪,硬是给忍了回去。
她被拎起来,解开绳子,让她自己站着。她感到自己非常虚弱,虽然他们仍然如临大敌,她却一点儿挣扎的心思都没有。
一条绳子从后向前兜在她的腋下,在胳膊上缠绕两圈,拴牢玉腕,然后向两边的木桩顶上一拉,她的双臂象鸟的翅膀一样向两侧张开着。接着两只脚腕也被拴住拉开,整个儿人形成一个巨大的「火」字形半悬在高台上空,只有两只大脚趾还稍稍挨在台面上。
「妖妇,你是不是后悔了,要是后悔了,我给你个痛快的。」
小军官看到姑娘的眼睛微有些潮湿,便引诱她服软。
冯婉玉得确很想快些死,她知道,只要她能说上一句背叛天国的话,他也许真的会一刀捅在自己的心窝,那个时候,她真的想求他们饶过自己的。但她马上就为自己的念头而感到羞悔了。她没有理那小军官,只是十分虔诚地望着天空,嘴里含叼着:「天父,请您原谅我,我不应该动摇对您的信仰。您是我永远的主,愿主拯救我的灵魂。阿门!」
在场的清兵都不是拜上帝会的人,信洋教的教民们当然不敢公然在这里看一个女人的光屁股,所以大家都不明白她说的是什幺,不过,至少知道她是在祈祷。清兵们其实也很迷信,一看她在那里念叼,还以为是在念咒作法呢,一个清兵惊呼道:「她会妖术,快别让她念。」
小军官眼疾手快,急忙一把捏住她的两腮,一用力,嘴就被迫张开了。
「快,把她的舌头拉出来。」小军官不敢放手,气急败坏地叫道。
清兵们急忙四下里寻找可以使用的钩子之类的东西,可惜急切间哪里找得到?
冯婉玉知道他要干什幺,她的两腮被捏得生疼,张开的嘴也闭不拢。她知道,一切不过是时间问题,慢慢等还不如快快死,于是自己把舌头伸了出来。
这回他们手里倒是有家伙事儿,赶快拿根小绳,把姑娘的舌头拴住,一个人在后面抱住她头,另一个人用力一拖,把舌头拉出来老长。
「噢——」一声惨叫,小军官把姑娘的舌头齐根割断了,血顺着嘴角流了下来。
冯婉玉疼得眼睛直向上翻,半天没喘上一口气来。
小军官从身边清兵手里接过一块白布,还有一小瓶白药,倒了一些在白布上,然后给她塞在嘴里。
「唔!唔!」姑娘只能从鼻子里发出惨哼了。
那美丽的躯体仍然在高台上扭动,小军官则绕到了她的身后。一个清兵帮着把两块雪白粉嫩的臀肉扒开,小军官则抓住那被小绳扎住的直肠一拉,右手刀一割,把小绳割断。稍停了一下,血慢慢地从那被切断的直肠断口上渗了出来。
小军官用手把套叠在一起的直肠捻开,然后把里面那一层抠出来,用另一根小绳一扎,绳头递在一个清兵手里。那清兵接过来,向外一拖,在女将痛苦的颤抖之中,一根软软的大肠便被从她的屁眼儿里拉了出来。
「好!过瘾!」围观的人真想不到,原来还有这样残酷的办法处置一个女人,人的肠子本身难得见到,更想不到肠子给拽出来了,人居然还活得好好的。
肠子在肚子里是盘曲的,从肛门中硬拉出来,难保不会在肚子里纠缠绞结,所以冯婉玉疼得扭动着,惨哼着,美丽的臻首拚命地摇动。清兵们从她的挣扎中感到了残忍的满足,他们把她的大肠小肠全都拉出来,一直拉到高台的后边,肠子最后绷得直直的,不再出来,他们知道差不多了,这才停手,把那扎住肠头的小绳切断。
剧烈的疼痛还在折磨着女将军,她呻吟着,暗自愤恨为什幺要生为女儿身。
没有了肠子,姑娘的肚子瘪了下去,生满耻毛的耻骨更显凸出了。
「咱们给她洗洗肠胃。」小军官说。于是,嘴里的白布被掏出来,不管好歹,一只早已准备好的铁皮大漏斗便塞了进去。有清兵在背后,一手抓着她那细长的脖子后面,一手扶着那漏斗,使漏斗直立着深深插进她的食管里。冯婉玉感到很恶心,但下面的屁眼儿一透气儿,想吐可是使不上劲,否则说不定呕出的东西就能把她呛死。
——
(八)
有个清兵提着几只大铁皮壶上来,往那漏斗里灌凉水,又一个清兵在下面把那肠子从屁眼儿那里开始往下捋。
要是正常情况下,水在人的胃里会停留二十分钟的时间,但这肠子一拉直,就上下通了,凉水直接就从肠子里流了出来,只见本来细细的小肠被水撑圆了,一个鼓包向下迅速移动,很快,一股黑黑黄黄的东西便从肠子的下口喷了出来,带着腥臭难闻的气味。
冯婉玉感到非常难过,但漏斗直接插在食道里,喊却喊不出来。
台下则是一片喝彩声,这种场面都是第一次见,心惊肉跳之余,又不免极度兴奋。
等下边流出的全是清水的时候,两大壶水已经灌完了。
清兵们并没有罢手,他们一边继续往冯婉玉的嘴里灌水,一边又把肠子的出口扎住,然后一小段一小段地用细绳捆扎。水不断地从上面流进肠子,把肠子撑圆,绳子一扎,一截儿一截儿的,活象灌肠一般。冯婉玉自己倒是看不见,因为都是在她背后进行的,她只知道自己的胃胀得难受,水开始灌不进去了,从嗓子眼倒流出来,清兵这才停止灌水。
绳子一直扎到女将的屁股下面,趁机休息了一阵了的小军官才过来一刀把肠子齐着她的屁股蛋儿割断了,水再次从下面流了出来,带着丝丝血迹。
「咱们下面怎幺办?」小军官把昨晚想好的程序给忘了。
「头儿,该这个了。」一个清兵把一只半尺来长,一寸粗细的竹管亮给小军官看。
「噢!想起来了。」
小军官说着,蹲下身去,把婉玉那用绳子扎住的半截子阴道解了塞回肚子里,将那竹管从阴户插进去。又去把那从屁眼儿里露出的肠子头了给塞回肚子里,并把透下的一点点直肠依旧捆好。
清兵又开始灌水,这一次水直接从肠子的断头流进了婉玉的肚子里。婉玉的肚子再次恢复了原来饱满的状态,而水则从下面直穿进腹腔的竹管里流了出来。
经受近半个时辰的折磨,冯婉玉的身体开始有些顶不住了,主要原因还是冰凉的水使她的体温下降得太多,嘴唇都发紫了。
清兵们看到要坏,这才住了手。因为怕她冻死了,又赶紧拿被子捂拿温水灌,一阵子胡折腾,也不知怎幺弄的,还真把她给救过来了。
这一回他们把她的嘴又给堵上了,为的是减少舌头的出血量。
刀拿在小军官的手里。他轻轻拍打着婉玉那因为水流尽而重新瘪下去的肚子,又用尖刀平着按在姑娘那雪白的乳峰上。锋利的尖刀将一股寒意带给女将,她不由打了个寒战,身子也挺直了。
刀刃在一颗粉红的奶头根部慢慢地来回蹭,婉玉努力让自己显得勇敢,但下面却满是尿意,好在刚才那一通折腾,她的尿早就合在凉水里流尽了,否则连她自己也不敢保证不会当众出丑。
小军官很随便地加了点儿力气,奶头便随刀锋而落,伴着鲜血掉在地上。
也许是被折磨得有些麻木了,过了好久,冯婉玉才感觉到疼,莺啼婉转地「嗯」了一声。
「好!要的!」台下的人群为她的勇敢和那美妙的痛哼而喝起彩来。
婉玉低下头去,心疼地看着自己那饱满的玉峰上失去了美丽的红珠,代之以一股赤色的山泉。接着,另一边也被割了下来。
她紧握着拳头,身体抽动着想缩成一团,但四肢都被绳子拉着,挣扎的结果,就只有两个脚掌短暂地离开了地面。
她为自己失去女人最迷人的地方而悲愤,心里很想哭,但只是眼圈微微红了,眼睛却干得难过,眼泪并没有流出来,她很庆幸天父没有让自己流泪。有天父在上面看着,她感到再大的痛苦,自己也能忍受。
小军官又把刀放在了那失去奶头的乳房根部,用刀尖从下向上深深地刺进去,一直刺到她的乳核下面,然后一边来回抽拉着尖刀切割,一边沿着乳根转了一整圈。
女将本来圆润的肢体都因为强烈的抽搐而显出一块块的肌肉,她的嗓子里发出压抑的低吼,但眼睛却不屈服地望着天空。
两只乳房被并排放在一只长方形的托盘里,奶头也被捡起来放进去,过一会儿会被送去给总督大人和一同监刑的大人们验刑。
——
(九)
冯婉玉站在台上,胸前留下两个大大的窟窿,血顺着雪白的肚皮流入两腿间的黑色毛丛中,然后从阴唇上那些向下生长着的阴毛尖上滴落到地上。
小军官站到一边,喝上几口从台下递上来的水,两个帮忙的清兵则接替了他的工作。
两个人一人一把刀,一左一右站好,然后从姑娘那圆圆的肩头下刀,分几刀把她的三角肌割下来。
接着,他们把她那扎住的直肠再次割开,塞回她的体内,从外面看上去同没动过刀时没什幺不一样,然后每个人往她的屁眼儿里狠狠地捅了一刀。
冯婉玉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从下面传来,来由「唔」地哼了一声。
清兵们从女将的臀股沟下手,从下向上把她那雪白的屁股割开,一边切,一边把她的臀肉向上掀起来,一到她的屁股被整个儿割下来,两块大大肌肉被扔在托盘上,同那女人的乳房摆在一起。
与捅屁眼儿相比,割屁股的痛苦可能要轻一些,所以,虽然切割是慢慢进行的,冯婉玉却紧咬着嘴里的白布,没有让自己哼出来。
接下来是关键的程序了。稍事休息的小军官回到台前,他站在冯婉玉的面前,先拔了那根竹管,轻轻摸了摸她那苍白但依然美丽的脸蛋,然后从下向上一刀捅进了她的阴户。
这一次是不能不哼了,她疼得直翻白眼儿,差一点背过气去。
台下的观众突然安静下来,他们还从没有见过人的肚子里面是什幺样子。
小军官的刀是两面开刃的,插在姑娘的阴户中,从前向后一推,把会阴剖开,姑娘的屁眼儿和阴户便连通了,再向回一拉,把冯婉玉的生殖器分成了两半,并一直割到心窝儿下面。
人们自然已经看不到肚破肠出的场面了,因为肠子早已经被从屁眼儿拉出来割掉了。没有足够的腹压,所以切开的肚皮只是靠着皮肤本身的弹性裂开了一条小缝,于是,两个助手不得不用两把铁钩子伸进去,把姑娘的肚皮向两边拉开。
肚子里已经是空空荡荡,肠子只剩下一尺来长,看得最清梦的是那块大大的肝脏,然后是已经瘪下去的胃。
小军官把那些内脏一件件从女人肚子里掏出来,每掏一件,冯婉玉就颤一颤,但却已经哼不出来了。
血象泉水一样开始从被切断的内脏动脉中喷出,在盆腔中汇集,然后从两腿间那被剖开的地方流下去。本来活蹦乱跳的女将军开始变得迷离,虽然身上的肌肉还在动,但头已经软软地垂下来,也不再出声了。
观众们看得出冯婉玉已经不行了,他们感到非常遗憾,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本来可以剐得再长些的。
一个助手拿了一根缝衣服针,弄火烧热了,然后往她的人中穴上捅了进去。
「唔——」冯婉玉拚命摇着头,又清醒过来,不过却没有力气把头抬起来,还是身后的清兵揪住头发,才把她的脸抬进来。
人们看到了一张痛苦扭曲的脸。他们虽然没有听到她大声的惨叫,但只凭这张脸,他们就知道她所受到的刑罚有多可怕。
「好了,算你行!老子们现在就送你上西天。」小军官说着。
冯婉玉努力睁开眼睛看着他,他弄不懂她的表情究竟意味着什幺,但接着,她突然笑了一笑。
小军官感到自己受到了莫大的嘲讽,人都快割烂了,她怎幺还能笑呢?
他无奈地把手从她肚皮上的大窟窿里伸进去,向上抠破膈膜,然后抓住了她的心。
那心依然在跳,他用力攥住她。
她突然睁大了眼睛,胸廓起伏着,仿佛窒息了一样用力喘了几口气,然后眼睛向上一翻,头又垂了下去。
冯婉玉被割了首级,挂在城楼前的旗竿上;她那割烂的身子就留在那台子上,验过刑的乳房、奶头、臀肉还有心肝五脏被放在托盘里摆在台边示众。
被用小绳捆扎成一小段一小段的肠子挂在台角。监刑的官员们刚走不久,那肠子便被人摘了去,放在地上一段一段地踩,听着爆裂的「啪啪」响声,仿佛是在踩鱼鳔一样,不过免不了弄湿了他们的鞋子。
百姓们很久都津津有味地品评着那女将的美貌,讲说凌迟的残酷,冯婉玉成了省城人最好的话题。
喜欢热闹的人们很快便又有热闹看了,不过这一次是长毛子打进了省城。除了总督大人只身逃走,其他官员和家眷都成了人家的阶下囚。
长毛子对杀他们人的人是决不手软的,于是,几个官员并他们的家眷便被绑到城门外剐了。
那一天省城的百姓们仍然人山人海地去看热闹。虽然长毛子剐人没有人家官军水平高,一个活人三下五除二就被卸作几块,但那情景也还是够惨,其实百姓们在其中得到了最大快乐并不是残酷和血腥。与看剐冯婉玉一样,他们更有兴趣的,便是那些被剐的官眷。官家的生活富足,官眷们也生得干净,那七、八个丰腴挺翘的姨太太和几个娇滴滴的官小姐们给人家剥了衣裳,一身肉白得象藕,嫩得象水葱一般,挺着一对对沉甸甸的奶,露着一丛丛黑茸茸的毛。在那法场之上,一个个赤条条的俏佳人儿被割了奶子,切开私处,鲜血淋漓,婉转哀号,那是何等样的风景。
只可惜他们的热闹看不长远。官军打回来的时候,长毛子紧守城池七、八个月,官军伤亡数万才得收复省城。进城之后,发了疯的官兵将全城百姓都当成乱民,不分青红皂白便随意屠杀,血流成河,年轻的女人们当然更不肯放过,尽管她们都赤裸裸地陈尸于街头,摆着各种各样下流的姿势,却再也没有百姓停下来欣赏了。
【完】